自驾阿姨苏敏丈夫首发声 其实分了更好何必绑在一起
导读:自驾阿姨苏敏丈夫首发声 其实分了更好何必绑在一起被媒体大量报道后,“苏敏”成为女性追求自我、追寻自由的代名词,一些追随者慕名而来。“自驾阿姨”不再指代一个人,而是变成一群人。苏敏开始接各种推广
苏敏在云南元谋县土林景区,独自操纵无人机拍摄短视频。现在,她在路上拍摄的短视频素材会上传到和家人共用的百度云帐号上,由远在郑州的女儿杜晓阳负责剪辑。关于一些拍摄的角度和风格,晓阳也会为苏敏提建议。两个人借由新媒体,建立起更亲密的连接,几乎每天都要打好几通电话。苏敏会每个月给女儿付一定的薪水,相当于以劳务费的形式,给外孙发点零花钱,“就当支持小家庭了。”
苏敏隐隐感觉到,女儿晓阳也因为自己做自媒体这件事,产生了一些变化。晓阳大学毕业后工作过一阵子,后来因为怀孕辞职,再也没有出门工作过。在郑州,她也不擅长与外人打交道,很多社交中断了,或者由丈夫刘伟伟代替。她每天的生活半径几乎只有养育小孩、照顾家庭。怀孕之后,她很少离开郑州。去年春节,一家人到海南找苏敏过年,是晓阳近几年去过最远的地方。
苏敏说,把剪辑的工作交给晓阳后,她会提出很多新鲜的点子。也会不断在网上学习,更新自己的思路。苏敏猜想,女儿在家里要照顾小孩,被琐事牵绊着,剪视频或许是她放松自己的一个窗口。白天俩孩子闹腾,她没有精力来做剪辑,一般会等到晚上,小孩睡觉了,整个环境静下来,再开始工作。
杜晓阳说,跟着妈妈的镜头,她像一起经历了那些风景一样。“之前大家都说广西桂林美,我印象中可能也就那样,但是当她把视频发过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这么美啊。我觉得好激动,也很向往。”
但其实独自旅行并没有看上去那样潇洒,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危险。有几次经历苏敏连女儿也没有详细讲过:在云南深山里,苏敏曾经迷过路。当天临近天黑的时候,她通过APP找附近的露营地,网络图片显示,50公里之外有片“生态露营地”,苏敏绕了一个多小时的国道到那儿,才发现情况不对:只有片像水草地一样的地方,在月光下泛着光,周遭空无一人。
天已经全黑了,山里也没有信号,她看到附近有亮着灯的房子,就下车去询问。推开门,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张大圆桌,几把椅子。她开始有后知后觉的恐惧,“没有狗叫鸡叫。喊了半天没有人”,她连转身都没有勇气,倒退着把门带上,退到车前,用手背着把车门拉开开始往外走,凭借记忆顺着原路返回。等折腾到附近的高速服务区,已经晚上11点多了。
留在郑州的丈夫
苏敏的旅程每天都在延续,丈夫却始终留在原点。
在迅疾的网络世界,他的公众形象鲜明而固定:一个在婚姻里实行AA制,擅长精神PUA并多次家暴的糟糕男人。咒骂与质疑从未间断。他没有公开回应过任何言论,像一团近在咫尺却面目模糊的影子。
12月初,我在郑州第一次见到了杜周城。他出乎意料地周到热情,始终笑眯眯的。他比苏敏大一些,今年62岁,留一头灰白的圆寸,脑袋和肚子一样饱满。
苏敏的故事在互联网上引起数次讨论,但在现实中,丈夫杜周城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他说自己没有直接看过相关报道,都是别人的转述,乒乓球的球友,或者小区邻居,有时候见到他会问一句:“嫂子开房车呢?”他会惊讶地反问,你咋知道?“我一般不会主动跟他们说。”
快90岁的姑父知道后把他喊到家里骂了一顿,“他说,看你俩过得啥这一辈子?去搭飞机到云南把她接回来。”杜周城一开始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是冷处理,“原来的事她既然说了,谁有法子?只能尽量往好处上想,原来的关系都落定了,只能以后关系维持好一点。”
但他始终没有“维系”的动作。“我也恼火,你说这过一辈子了,我自己在这天天做饭,我也够难了。”最开始,他以为苏敏只是短暂地离开,最多一两个月就回来了,没想到她决心那么大,接近两年没回郑州,“把外边儿当个家了。”
现在,他一个人住在三室一厅的房子里,觉得自己越过越“独”了。虽然两个人以前也是分房间睡,总是吵架,但屋里总能有个声响。现在整个房子空空荡荡的。
杜周城把时间大量消耗在乒乓球和广场舞上,上午参加中老年组的练球,晚上准时出现在跳舞小广场,下午他一般窝在沙发上看电视。中央四套,固定频道。“有时候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醒了再接着看。”
他并非完全不关注苏敏的消息。他对各类APP不熟悉,安卓机上自动安装了许多软件,他从来没点开过。但最近两年,他学会了使用抖音,并在上面关注了苏敏的账号。偶尔,他会在上面搜索“五十岁阿姨自驾游”,看看苏敏到哪儿了。
但他几乎没有主动询问过对方的近况。以前因为ETC卡绑定的是他的银行卡,他还会在扣除金额大于100元时给苏敏打个电话。后来苏敏换了房车,卡也换成了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彻底断了。
至于这段让苏敏感到痛苦失望的婚姻,在杜周城看来,已经是还不错的结果了。他参照的坐标系是他的兄弟们,“我们家弟兄仨,老二老三都离婚了,我没离婚”,他觉得这意味着某种成功。
关于动手打人这件事,他承认自己实在控制不住情绪,“有时候吵烦了,她一顶嘴,我容易控制不住(动手)。”但这些在他的观念里都是“平平常常”的事,“在家里哪有不‘叮咣’的?”
他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父母也会吵架,吵急眼了也要动手。说自己是在几个兄弟里挨打最多的那个,用鞋拖,或者木杆。“农村的三间房是通房,房子当中是个门。那时候都没有锁,都是门串子。然后(父母)叫到屋里头串上门,打得再疼再狠也跑不掉。”
和苏敏出身城市不一样,杜周城家庭条件很差。他至今记得那种苦,当时农村分给各户的油很少,他们大部分的食物都是红薯干或者红薯面做的馒头。在厨房的梁条上系绳子,绳子末端挂钩,大家会把红薯和馒头挂在上面,防止被老鼠偷袭。他总是祈祷别下雨,不然红薯面会发霉。从家到学校有十几公里,他家里没有自行车,不论冬夏,都需要背着馒头步行去学校。
少年杜周城有次嘴馋,用罐子加盐,又偷了一点油,加水和好,用来蘸馒头吃,“又咸又香”。不巧被二弟发现了,给他吆喝了出去:“杜黑子偷吃油!”(他因为肤色被叫做“黑子”)
童年的艰苦让他非常看重金钱。不仅要有钱,还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结婚后不久,苏敏从化肥厂下岗,到郑州找他,两个人开始一起生活。他算计着开销,每笔钱花到哪儿都要问清楚。
这让苏敏一度感觉到痛苦,后面两个人发展成AA制,各管各的钱。杜周城说,自己这么做还有一点私心,“她家好几个兄弟,也不咋上班,(AA)我起码能控制点,可能她给家里帮助少一点。”
苏敏与她的新房车,这晚她将在土林景区内露营。我问他,有没有想过这样的算计会影响两个人的关系?他沉默片刻,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这个确实没有”,他说,自己脑子里没有沟通的概念,“你现在提出来,我觉得有点遗憾了,我确实没有往这个上面想过,就觉得到底是一家人,没有那么多规矩。”
和在农村成长的同龄人比较,他说自己算得上“混得不粗”,一路还算顺遂,最终以事业编的身份退休,每个月能领五六千块退休金。1978年高中毕业后,他先去了兰考县打零工,做给铁门除锈的手工活。后来听说郑州黄河河务局招工,他顺利入选,也从非正式的零工转为了正式工,在河务局呆了整整40年。
他在河务局做过很多类型的工作,发电机组维修工、防汛一线,但他最喜欢的工作还是给领导开车——这个活不大用讲话,保守领导的秘密是胜任这个岗位的必备要素。
在单位里,杜周城很少参加酒局,他不大能喝酒,也不怎么抽烟。偶尔参与聚会,他是坐在边角默默吃菜听着的那个角色。
“不会说话”的特质延伸到家庭内部,表现是他总是挑三拣四,“说话带刺儿”。他说自己有时候一句话说出口也会后悔,但在当下那一刻,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挽回。出于一种男性的自尊,他从未向妻子和女儿道过歉。“我在外边也这样,有时候说话不带刺儿,但别人听起来就是不太得劲。”
-
 小伙给父亲墓碑贴二维码 这个有点磕碜人2023-03-28 22:15:16小伙给父亲墓碑贴二维码 这个有点磕碜人在重庆的龙潭山陵园内,有一座新立的墓碑,除了记载了逝者陆志富的简短生平,上面还贴有三组二维码。许多前来追思和悼念他的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小伙给父亲墓碑贴二维码 这个有点磕碜人2023-03-28 22:15:16小伙给父亲墓碑贴二维码 这个有点磕碜人在重庆的龙潭山陵园内,有一座新立的墓碑,除了记载了逝者陆志富的简短生平,上面还贴有三组二维码。许多前来追思和悼念他的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
 阿黛尔无限期中止职业生涯 是瘦下来了中气不足吗2023-03-28 21:50:46阿黛尔无限期中止职业生涯 是瘦下来了中气不足吗不少网友表示:“早就财务自由了,想干嘛就干嘛”、“有点可惜但希望可以尽快调整好状态”、“希望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去听一场演唱会,毕生的梦想了”、“我还没看过阿呆演唱会呜呜呜
阿黛尔无限期中止职业生涯 是瘦下来了中气不足吗2023-03-28 21:50:46阿黛尔无限期中止职业生涯 是瘦下来了中气不足吗不少网友表示:“早就财务自由了,想干嘛就干嘛”、“有点可惜但希望可以尽快调整好状态”、“希望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去听一场演唱会,毕生的梦想了”、“我还没看过阿呆演唱会呜呜呜 -
 国际机票再现“白菜价” 三桶油后面站着一把镰刀2023-03-28 21:45:54国际机票再现“白菜价” 三桶油后面站着一把镰刀 社交平台上,不少留学生感叹近期回国机票降价,日本留学生刘颖见证了回国直飞机票从万元一路下降,“去年12月就能买到五六千回国的机票了
国际机票再现“白菜价” 三桶油后面站着一把镰刀2023-03-28 21:45:54国际机票再现“白菜价” 三桶油后面站着一把镰刀 社交平台上,不少留学生感叹近期回国机票降价,日本留学生刘颖见证了回国直飞机票从万元一路下降,“去年12月就能买到五六千回国的机票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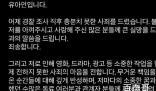 刘亚仁发长文就吸毒事件道歉 目前警方正在讨是否对刘亚仁进行逮捕2023-03-28 21:37:48刘亚仁发长文就吸毒事件道歉 目前警方正在讨是否对刘亚仁进行逮捕刘亚仁在调查结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因不光彩的事情而站在这里,让支持和喜欢我的广大观众深感失望,就此深刻反省检讨
刘亚仁发长文就吸毒事件道歉 目前警方正在讨是否对刘亚仁进行逮捕2023-03-28 21:37:48刘亚仁发长文就吸毒事件道歉 目前警方正在讨是否对刘亚仁进行逮捕刘亚仁在调查结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因不光彩的事情而站在这里,让支持和喜欢我的广大观众深感失望,就此深刻反省检讨 -
 姐弟坠亡案母亲再发声 内幕曝光引争议2023-03-28 21:32:24姐弟坠亡案母亲再发声 内幕曝光引争议直至2023年2月13日,生母陈美霖再次发声,人们才得知:张波和叶诚尘仍然怀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不惜在短短一个月内连续写了三封狱中来信
姐弟坠亡案母亲再发声 内幕曝光引争议2023-03-28 21:32:24姐弟坠亡案母亲再发声 内幕曝光引争议直至2023年2月13日,生母陈美霖再次发声,人们才得知:张波和叶诚尘仍然怀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不惜在短短一个月内连续写了三封狱中来信 -

-
 白狐胖成煤气罐是为御寒 存在减肥失败的情况么?2023-03-28 21:21:24白狐胖成煤气罐是为御寒 存在减肥失败的情况么?不过,最近一段山东威海神雕山动物园的白狐视频在网络上走红,却带来了强烈的反差感
白狐胖成煤气罐是为御寒 存在减肥失败的情况么?2023-03-28 21:21:24白狐胖成煤气罐是为御寒 存在减肥失败的情况么?不过,最近一段山东威海神雕山动物园的白狐视频在网络上走红,却带来了强烈的反差感 -
 酒店回应成年子女不能与父母住标间 人家爱怎么住怎么住2023-03-28 21:17:10酒店回应成年子女不能与父母住标间 人家爱怎么住怎么住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北京速8等知名连锁酒店,工作人员也是明确表示“已经成年的一家三口不能住同一间标间”,建议多订一间房或者预订家庭房型
酒店回应成年子女不能与父母住标间 人家爱怎么住怎么住2023-03-28 21:17:10酒店回应成年子女不能与父母住标间 人家爱怎么住怎么住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北京速8等知名连锁酒店,工作人员也是明确表示“已经成年的一家三口不能住同一间标间”,建议多订一间房或者预订家庭房型 -
 24岁女孩入职体检查出少一个肾 背后的真相让人震惊2023-03-28 20:52:2824岁女孩入职体检查出少一个肾 背后的真相让人震惊生存率与年龄和性别匹配的正常人相近;但患者肾功能障碍、蛋白尿和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及终末期肾病发生率相对较高,因此需注意定期观察体检。
24岁女孩入职体检查出少一个肾 背后的真相让人震惊2023-03-28 20:52:2824岁女孩入职体检查出少一个肾 背后的真相让人震惊生存率与年龄和性别匹配的正常人相近;但患者肾功能障碍、蛋白尿和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及终末期肾病发生率相对较高,因此需注意定期观察体检。 -
 男子晒9本结婚证8本离婚证 背后的真相让人目瞪口呆2023-03-28 20:47:14男子晒9本结婚证8本离婚证 背后的真相让人目瞪口呆近日,一则关于一名27岁男子晒出自己9本结婚证和8本离婚证的新闻,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男子晒9本结婚证8本离婚证 背后的真相让人目瞪口呆2023-03-28 20:47:14男子晒9本结婚证8本离婚证 背后的真相让人目瞪口呆近日,一则关于一名27岁男子晒出自己9本结婚证和8本离婚证的新闻,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